作者:林少雄(上海大學教授)
學人小傳
王振復,1945年生于上海。1964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1970年畢業留校,在職期間獲文學碩士學位。長期從事易學、巫文化學與美學、中國美學史、中國佛教美學、中國建筑文化與美學等領域研究。撰有《巫術:〈周易〉的文化智慧》《〈周易〉的美學智慧》《中國美學的文脈歷程》《中國巫文化人類學》《中國巫性美學》《中國早期佛教美學史》《建筑美學》《中華古代文化中的建筑美》等40余部著作,主要學術成果收錄于《中國文化美學文集》(八卷)。

圖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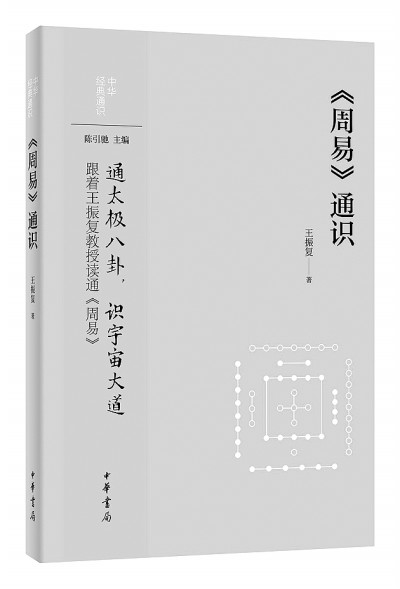
王振復的部分著作 圖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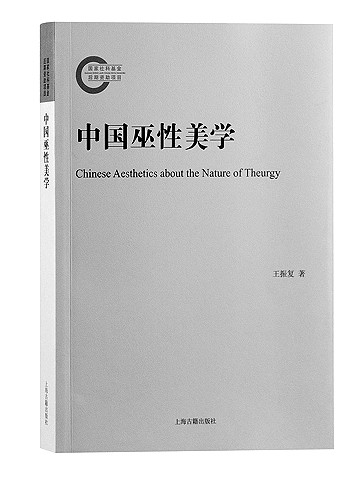
王振復的部分著作 圖片由作者提供

王振復的部分著作 圖片由作者提供

王振復(右)與本文作者在一起。圖片由作者提供
在迄今60年的學術人生中,復旦大學王振復教授專注于中國文化美學研究,始終思考著中國美學的人文“根因”“根性”問題——“中國審美”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他自謙,自己是一個極普通的讀書人,一生都在一次又一次學術性試錯與糾錯的過程中掙扎與努力,撰寫的40多部著作,無非記錄了一些人生過程。其實,那些著述既是他人生過程的記錄,也已融入他的生命,成為人生的一部分。
機緣特出 情系美學
一個學者對學術之路的選擇,除了專業興趣有關,還需要一些特殊的機緣。
王振復先生1945年出生于上海,家境貧寒,生下來就沒見過祖父,三歲失怙,體瘦身弱,一生病,不是去刮痧就是通過吃香灰“治病”。他自小性格內向、敏感。當別的孩子在踢毽子時,他會為夕陽西下的沉寂與悲壯而傷感、震撼,“殘陽的美,卻同樣讓我有些感傷地體會到一抹深沉的輝煌,那是一種沉雄而悲劇性的力量”;當別的孩子跳繩時,他會為墜落天井的一片枯葉而盡夜牽腸掛肚,“一張枯葉打著旋兒、從空中悠悠落下,終于落在天井的一角不再飄動,不由讓我對此盯住看了許久。晚上睡覺時,還一直牽掛這件小事,總也放心不下。第二天,我拂曉就起床,第一件事,便是趕快到天井里去,看那片落葉究竟還在不在那里”。王先生回憶,還未上小學時,聽哥哥朗誦臧克家的《老馬》,他能從中感到詩人對忍受苦難的農夫的深切同情,“詩境的沉郁,與我所經歷的苦難童年以及偏于沉靜的個性相應。沉潛與平淡,幾乎是我一生的心境,而內心并非涼薄與枯寂”。
也許是這種生活經歷,他從小就對生命、對不可捉摸的命運有了好奇,這成為他后來研究巫術、《周易》的淵源。祖母一心向佛,耳濡目染,他從小就對佛教有了額外關注,這也正是他多年來“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根本動因:“盡管我年輕時最心儀的是佛學與老莊之學,但首先還是要努力弄通作為本人學術之本的易巫之學,爾后擴大到同是巫學而更為原始、古老的甲骨占卜之學,同時不忘釋迦與老莊。盡管在學術上,我主要研究的是易學與巫學,似乎很入世,但實際上我的心靈深處是相當向往佛禪與老莊之學的。”
1964年,王先生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入學不久,他在圖書館讀到《美學問題討論集》,從此就對美學著了迷,這套書成為他學習美學的啟蒙讀物。1970年,王先生畢業留校在政宣組工作,1973年回中文系任教,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有兩個幾乎伴隨我一生的‘密友’,一是書籍,二是疾病。”出于持久的愛好與執著,王先生從事學術研究,“欣欣然于晉人王子猷般‘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的情趣”,從沒有“成名成家”的功利目的。對他而言,治學如為人,學術即人生。他的著述,也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成果,而是呈現出鮮活的生命質感與飽滿的情感狀態。
博觀約取 圓融自洽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提出,史家應有才、學、識“三長”。王先生認為,所謂“識”,是指在具備一定“才”“學”的前提下,能夠在某一學術領域,做到有所發現、有所創新,發現問題、論證問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問題。這可以視為王先生的夫子自道。
王先生推崇復旦大學陳允吉先生對陳子展先生治學經驗的總結:“‘博觀’是手段,‘約取’是目的;‘博觀’是奠基,‘約取’是在基礎上進行建筑;‘博觀’是增加感性認識,‘約取’要經過理性的思考。”在王先生看來,“凡讀書做學問,須如書寫‘T’那樣,先橫一筆,再豎一筆,才得寫成一個‘T’。橫筆,指廣泛閱讀與披覽;豎筆,指深入于某一學術領域的閱讀而努力深研。橫為前提,豎則圓成,否則一事無成。憑興趣廣泛閱讀,未必皆為好事。”他研究中國文化美學的“根因”“根性”,就是以對中國傳統經典以及西方哲學、文化學、人類學、神話學經典著作的廣泛閱讀為“橫筆”,通過對《周易》等人文經典的精讀、思考,努力深入于易、巫美學的研究。
在《周易》中,他拎出“吉”“兇”二字,認為“吉是真善美的歷史與人文原型;兇是假惡丑的歷史與人文原型”,由此推斷,在《周易》巫筮以及更為古老的甲骨占卜等的吉兇意識中,早已孕育著可以生成美丑以及真假、善惡的歷史與人文因素,“因此,將《周易》美學的研究拓展到‘作為文化哲學的美學’而追溯其本根、本性,是可能的”。
王先生意識到,盛于殷代的甲骨占卜及其文字所蘊含的原始審美意識比《周易》更為原始。于是,數十年間,他通過對甲骨文及《說文解字》的研讀,強化學術研究的“根因”與“根性”。從文字學與詞源學的視角出發,王先生對一些中國哲學與美學特有的詞語及其范疇進行闡釋,頗見新義。如對“大”的釋讀:他認為,《道德經》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方無隅”“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強為之名曰大”,《易傳》的“大哉乾元”,“天地之大德曰生”,這些詞句中的“大”皆非大小的大,而是“太”的本字,指萬物本根本性的“道”。《說文》:“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從十從一。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結合對甲骨文的釋讀與古籍中“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等記載,王先生得出中國文化中的“士”原型為“巫”的結論。
對傳統文獻的精讀、考據、梳理,是王先生聰慧之才、厚實之學的展現,也是他莊嚴的學術基底,為他溯源中國審美意識提供了有力支持。
過去一些易學學者專注于對《易傳》道德人格的討論,這雖然是一個很好的視角,但王先生另辟蹊徑,從《周易》象數之學與卦爻辭的文脈聯系中,努力發掘原始易理的巫性特質與人文底蘊,由此探索中華原始審美意識的發生,進而提出“中國巫性美學”這一重要學術命題,做成了具有學術創見的本土化的美學“新品種”。
西方文化人類學一般將原始神話、圖騰、巫術統稱為“神話”,這是“廣義神話說”。王先生提出“狹義神話說”,將神話、圖騰、巫術這三種人類最早出現的原始文化形態稱為“原始信文化”。巫術本是虛妄而難以奏效的,初民卻信以為“真”,體現了初民向野蠻自然進擊時,不得已而又盲目的原始努力。他認為,中國文化與美學的根本特質主要是從原始巫文化的母胎里孕育而成的,中國巫性文化的所謂“巫性”,是畏天與知命、神性與人性、媚神與瀆神的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且以前者為主。中華巫文化源遠流長、影響深巨,其傳統因素幾乎融入人文科學的一切領域,參與了中國古代哲學、政治、歷史、道德、藝術審美與民間風俗等基本人文品性的生成。中國美學基本而主要的歷史與人文素質,起始于原始巫文化的原始“實用理性”。這一“實用理性”,一般總是與中華審美糾纏不清,便是所謂“美善不分”“盡善盡美”,成為拒絕與消解宗教的精神之力。中國美學的根本素質,并非“以美育代宗教”,而是“以倫理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
在中國美學史研究中,王先生把中國的文化、哲學及其美學歸納為“有”“無”與“空”三大分支,即儒有、道無、佛空,三學會通。此雖為一家之言,但竊以為能夠做到提綱挈領,綱舉目張,學理自洽。通過對《周易》與巫術的研究,王先生認為,“風水”是一種文化迷信,是“古人以命理理念,認識與處理人與環境之關系”的一種文化現象,把古代“風水”界定為“樸素而粗糙的環境學、生態學”。這一論證,準確新穎,既揭示了“風水”迷信的本質,也賦予這一中國特有的文化范疇以美學意蘊與氣象。
在易學、巫文化學、佛教美學之外,王先生還傾心于建筑美學研究。這源于青年時代“愛的諾言”。“我走上研究中國建筑文化之路,與妻子楊敏芝直接有關。她研究生畢業于同濟大學建筑學系。記得初次結識時,她說要向我學習文學,我便隨口說:‘那我也來向你學習建筑吧。’豈料,就是這一句平常的話,成了我一生的信言。我因此讀了不少古今中外有關建筑文化的書。”通過對建筑這一獨特“文本”的閱讀,王先生從傳統學術對“心”的研究開始轉向對“物”的研究,得出“宇”的本義為“屋檐”,“宙”的本義為“屋梁”的結論。他認為,“宇宙即建筑,建筑即宇宙”,中國建筑文化的時空意識及其理想在于象法自然宇宙、自然時空,建筑作為人文“宇宙”,不僅有關“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且是中國人所領悟和理解的時空哲學及其美學。這種解讀將建筑文化上升到中國文化、藝術與美學中時空觀念的根本層面,具有原創性意義。
通過對《周易》長期而深入的研究,王先生得出“原始易學是巫學”的觀點。這個觀點不僅揭示了《周易》的美學特質,而且延伸到對建筑美學、佛教美學、中國美學史的研究與書寫。在建筑美學中,他認為,作為迷信的“風水”,摻雜著古人的巫性意識;在佛教美學中,他在人性與神性之間發現并建構出“巫性”,在崇拜與審美之間發掘出“詩性”。這種梳理與建構,使得王先生所從事的數個看似迥異的研究領域建立起緊密的邏輯關系,構成一個圓融自洽的學術體系。
沉潛思考 詩意為文
在研究立場和方法上,王先生選擇了“學院派”的道路,追求歷史與邏輯、實證與理念的統一,治學力求“歷史優先、回到文本”。在學術表達上,他強調詩性與思性的統一。王先生的學術研究,具有深度與穿透力,也融入了個人的性情。我讀王先生的文章,如同與他本人交往一樣,常常有如沐春風的感受,能從他通俗又富有哲理的語言中,體會到詩意與美感。
對王先生來說,詩意不是任何刻意外加的東西,而是源自先天的靈慧與生命深處的一種本能的飽滿與愉悅。他的詩意,經過智慧之思的滋潤與撫慰,無指涉性、無對象性、無功利性,捕捉著情感的走向,描摹著精神的形態,謳歌著生命的悅樂。他撰寫過《詩性與思性:中國美學范疇史的時空結構》一文,從學理層面將“詩性”與“思性”作為對偶范疇進行梳理與辨析:“詩性的思性化,思性的詩性化,是中國美學史一系列名詞、術語、命題、范疇及其群落之概念、觀念與思想、思維的顯著特點。”
記得1992年,我研究生入學不久,有一次王先生和我談到學術論文的寫作,說最好可以一次成稿。我頓時感到壓力很大,覺得這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后來,見到王老師幾十頁的文章手稿,字體類似顏體楷書,一筆一畫,沒有一處連筆,中間似乎只改了一個字,我極為震撼。從此以后,我開始注意落筆前的資料消化與構思醞釀,胸有成竹后才動筆寫作,我后來的教學與科研都受益于這方面的訓練。隨著技術的進步,當下,散漫式思考、零碎式表達更為常見,但竊以為這種系統收集材料、構思作文的學術訓練,仍然十分必要與重要。蔣孔陽先生在為王先生《〈周易〉的美學智慧》所寫的序言中,稱贊王先生“不僅勤學深思,而且思路敏捷,出手甚快”。當然,這不是說王先生為文全都是一次成稿,一些重大、復雜的文章,他甚至不惜“十年磨一劍”。如《論崇拜與審美》一文,“寫得尤為艱苦而歷時漫長,從1983年暑期開始,一直到1990年的冬天(發表于《學術月刊》1991年第7期)。所搜集的資料,不下四五萬字。八年間,反復重寫與修改了九次,僅僅一個開頭,反反復復弄了數十稿,浪費了許多稿紙(當時是500格的手寫稿),一直到自己稍稍滿意為止”。從這云淡風輕的敘述中,我們不難體會到學術之“思”的無限魅力,以及“思之不得”時的“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與“思之既得”的神清氣爽。
《巫術:〈周易〉的文化智慧》是我最早讀到的王先生的著作。因為此前所受教育,我們這一代人對傳統典籍帶有諸多誤解,我總覺得《周易》帶有一種無法言說的“邪氣”與“晦澀”,面目難辨,恍如天書,所以有意無意敬而遠之。經歷過此前“文化熱”與“美學熱”的烘烤,見到此書書名,我頓時覺得親切無比,及至展卷讀書,時時被王先生的細密思維與盎然詩意所驚艷。接下來讀《〈周易〉的美學智慧》,我更是嘆服不已。過去,我雖然也喜歡理論,但有一種刻板印象,那就是理論著作都是晦澀難懂的。特別痛苦的一次閱讀經驗,來源于大一暑假時閱讀黑格爾三卷四冊的《美學》,書中的每一個字我都認識,但就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我雖然咬牙讀完了全書,讀完后確實覺得眼界有所拓展,但閱讀過程的痛苦至今記憶猶新。可是讀到王先生關于《周易》的這兩本書,我卻感到趣味盎然、滿目蔥郁。這兩本書,我碩士階段讀過兩遍,博士階段又讀了兩遍,近兩年再次重讀,仍然滿目蔥郁(“蔥郁”也是王先生喜歡使用的一個詞)。這里不妨隨手引用一段:
“依稀踏進青泥盤盤、幽靜古樸的窄巷小弄,撫摸被悠悠歲月無情侵蝕的殘垣斷壁,那濃得化不開的古老氣息,令人驟感現代生活的快速節奏突然變慢了,整個心靈因而沉寂寧靜下來,好像實現了對中華古代文化一種情感上的‘皈依’,也不免有一點苦澀的滋味浮上心頭。因為從文化整體來說,《周易》巫術給我們提供的文化信息畢竟過于陳舊了。而穿過泥濘的沼澤、小徑,拂去歷史的塵埃,這里是一個偉大心靈的‘宇宙’。不只有愚昧和稚淺,有黎明前的黑暗,有撕肝裂膽的痛苦與憂患;也有生的喜悅、愛的掙扎,有詩的韻味,有滿天云霞,一泓‘微笑’,有長河的奔涌,大地的磅礴,光輝的日出!有天籟、地籟與人籟的交響,有轟轟作響的來自遠古的回聲……更有《周易》原始巫術文化的童蒙智慧猶如晨星閃爍,撩人心魄,它牽引我們上下求索的文化心魂跋山涉水,尋訪探問,漸入佳境。”
王先生不是詩人,卻詩意地生活著、研究著、寫作著。詩人從日常生活中升華出詩意,而王先生通過詩意來理解與觀照日常生活。
謙謙君子 與人為善
“見到大先生(王先生祖母對小學老師的尊稱),一定要磕頭,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儂要好好讀書啊,讀好書才有飯吃。”“儂已經長大了,要好好學會做人。做人要實實在在,對人對事,要誠心誠意。”“儂勿可以隨便要別人家的東西。”……王先生自幼受祖母教誨,為人處世文質彬彬,謙和不爭,與人為善。他從不為自己的事求人,別人的事則盡力幫助,凡事都不愿給別人添麻煩。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王先生,我以為非“君子”二字莫屬。
20世紀90年代,王先生當時身體很差,教學任務又很繁重,想在學校申請一間公寓房用作中午休息,申請數年,毫無結果。我見他疲憊異常,就斗膽提出建議:當年與王先生一起考入復旦的一位中學老同學,當時正在負責學校一些方面的工作,不妨找找這位老同學,應該可以解決問題。可是,王先生拒絕了。無論遇到什么生活方面的困難,他從不向組織提出來,包括這個老同學。后來有一個寒假,弟弟要結婚,我買不到回老家的火車票,百般無奈之下給王先生打了個電話,他說試一試。當晚,王先生回了電話,說搞到了一張到天水的車票,離我老家隴西不遠。細問原委才知道,王先生給他那位老同學打了電話,剛好學校招待所有一張富余的車票,可以讓我先拿去用。我后來感到十分內疚,因為自己的私事,破壞了導師的規矩。
復旦大學陳引馳教授與王先生相識幾十年,斷斷續續有很多交往,他從來沒有聽王先生議論過什么人、批評過什么人,“有時候,我聽得出王老師有意見,但他從來都是非常溫和的,‘口不論人過’。與之相應,在學術研究中,他的狀態就是埋首典籍、甘為書生。不管在職的時候還是退休后這么些年,他一直在做學術,以學術為自己的生命”。王先生自己則認為,讀書與寫作,雖然很辛苦,但也很幸福,當讀書與寫作成為一種日常的生活方式與情感表達方式時,其他方面就顯得很不重要了,“研習學術,唯在持久堅持的‘三要’:讀、思、寫。讀是基礎;思是關鍵;寫是落實。假如沒有宗教般的強烈興趣和執著,這一‘三要’,是可能會落空的”。可見,對于王先生而言,學術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修行。當一種職業選擇成為信仰,那么這一工作就具有了某種崇高與神圣性。日常生活因學術而顯得充盈飽滿,學術因信仰而散發出神圣迷人的輝光。
近二十年來,王先生選擇了退而不休、閱讀無止、筆耕不輟的生活方式,不謀稻粱,不為功名,為了思想的表達與學術的傳承,安貧樂道,在自己的領地上努力耕耘。這種學術人生,是一種美妙的生活與生命形態;這種獻身學術的精神,是一種特別的審美精神。王先生及其學術,真可謂“思詩合一,向美而生”。
《光明日報》(2024年06月24日 11版)
